一般情况下,行政机关中止行政程序的行为只是一个过程性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当行政机关的中止行为实为拖延履职或者拒绝履职时,则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成为可诉的行政行为。
【基本案情】
一工程项目系由A公司承建,随后,A公司又将此工程项目的劳务分包给B公司,工期为2016年4月28日至2018年6月30日。
2016年11月8日,陈某经人介绍到工程项目工地做木工。同月10日上午11时左右,陈某在工地8号楼作业时,因躲避塔吊快掉下的钢管时摔倒受伤,经×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断为右侧第6、7、8肋腋段骨折。
2017年3月8日,陈某向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同年3月30日,该局向B公司作出《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该公司收到通知书后,向人社局提交了《回函》,称其与陈某不存在劳动关系。同年4月15日,人社局向陈某作出《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三款、《工伤认定办法》第二十条之规定,决定中止工伤认定,待提供相关证明后恢复工伤认定程序。
陈某收到该中止通知书后不服,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按例说法】
一审法院:人社局尚未作出任何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即得出双方劳动关系无法判断的结论,违法
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的规定,人社局具有对工伤认定申请作出相应处理的法定职责。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2009)行他字第12号《关于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确认权请示的答复》载明:“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受到伤害的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根据该答复内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依法具有认定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而认定伤者与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则必须基于一定的事实。《工伤认定办法》第九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可以根据需要对申请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调查核实。”第十一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在工伤认定中,可以进行以下调查核实工作:(一)根据工作需要,进入有关单位和事故现场;(二)依法查阅与工伤认定有关的资料,询问有关人员并作出调查笔录;(三)记录、录音、录像和复制与工伤认定有关的资料……”。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可以根据需要而进行调查核实,查清事实,开展调查是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法定职责。陈某已向人社局提交了证人证言、劳务分包合同、诊断证明等证据材料,B公司亦提供了一份《回函》,而人社局却未对当事人双方及相关证人作任何调查核实,在缺乏相关事实的情况下,即得出双方劳动关系无法判断的结论,并以此为由作出工伤认定中止决定,属于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依照相关规定,判决撤销人社局于2017年4月5日作出的《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人社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针对陈某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提起上诉:陈某是否是B公司承包的建筑工地上的工人,是否与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是否在工程项目工地做工等事实均无法确认
人社局履行了调查核实工作职责,为了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人社局才做出了本案被诉的工伤认定中止决定。
二审法院: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发现劳动关系存在争议的,有权进行调查核实,也有权作出认定
另查明:2017年12月5日,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恢复通知书》,对陈某工伤认定申请恢复调查。2017年12月27日,人社局提起本案上诉。2018年1月10日,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载明:“经调查核实:该案件现已进入司法程序。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三款、《工伤认定办法》第二十条之规定,决定中止工伤认定,待提供相关证明后恢复工伤认定程序”。
二审询问中,双方对本案被诉《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作出前,人社局口头告知陈某就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申请劳动争议仲裁、陈某明确拒绝的事实无异议。
法院认为,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的规定,人社局具有对工伤认定申请作出相应处理的法定职责。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人社局作出本案被诉《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中止工伤认定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作出工伤认定需要以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结论为依据的,在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尚未作出结论期间,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时限中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进一步明确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发现劳动关系存在争议且无法确认的,应告知当事人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在此期间,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时限中止,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当事人。劳动关系依法确认后,当事人应将有关法律文书送交受理工伤认定申请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该部门自收到生效法律文书之日起恢复工伤认定程序”。据此,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中,可以依法中止工伤程序,但必须符合前述法律规定的条件,即“需要以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结论为依据”,具体而言,当劳动关系存在争议时,还必须满足“无法确认”这一条件,而且,是在当事人选择了仲裁的情况下,在仲裁期间方可中止。
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伤认定办法》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有权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也有权对申请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调查核实。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2009)行他字第12号《关于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确认权请示的答复》明确:“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受到伤害的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按照上述规定,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发现劳动关系存在争议的,有权进行调查核实,也有权作出认定。这一方面是劳动行政部门的行政职权,同时也是其法定职责。既然为其法定职责,则应当依法履行。本案中,陈某在申请工伤认定时,提交了证人证言、《劳务分包合同》等证据材料以证明其劳动关系;而对陈某不是工伤负有举证责任的一审第三人B公司,在收到人社局依法送达的《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后,仅向人社局提交了《回函》,陈述其与陈某不存在劳动关系,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人社局如认为劳动关系存在争议,应当对陈某提交的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对其劳动关系争议作出认定。只有当劳动关系无法确认时,方可告知被上诉人陈某可以申请仲裁。但人社局在本案中举示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进行了相关调查核实,更不能证明争议的劳动关系无法确认。在此情况下,人社局告知陈某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并不符合前述法律规定。
再者,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的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告知申请仲裁后,当事人“可以”申请仲裁而非“应当”申请仲裁,当事人对此有选择的权利。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在挂靠、转包等特殊情形下,工伤认定不以是否存在真实劳动关系为前提。因此,本案中,在陈某已经向人社局明确表示拒绝申请劳动关系仲裁的情况下,人社局应当依法履行调查核实和认定的职责,其中止工伤认定程序,实质是拖延履行对陈某进行工伤认定的法定职责,这将导致陈某的工伤认定程序无法进行下去,对陈某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质影响。因此,虽然一般情况下,行政机关中止行政程序的行为只是一个过程性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当行政机关的中止行为实为拖延履职或者拒绝履职时,则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成为可诉的行政行为。一审法院对人社局作出的中止行为进行实体审理并作出撤销该中止通知书并责令限期作出行政行为的判决,并无不当。
此外,一审判决作出后,人社局于2017年12月5日以《工伤认定恢复通知书》对陈某工伤认定申请恢复调查。之后,又于2018年1月10日作出《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再次决定中止工伤认定,行政行为随意而不严肃,实属不当。
【小编有话】
一般情况下,工伤认定必须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但是,并不是所有情形都的存在劳动关系。比如,本案即属于其中一种情形之一,在挂靠、转包等特殊情形下,工伤认定不以是否存在真实劳动关系为前提。再比如,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农民工受伤,工伤认定一般亦不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

 生活常识网
生活常识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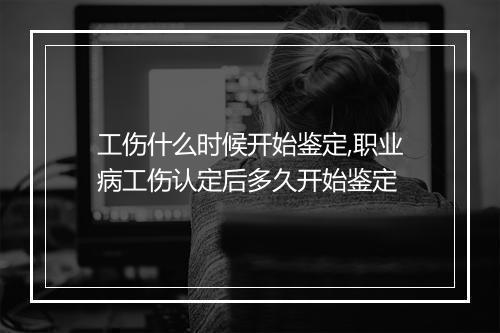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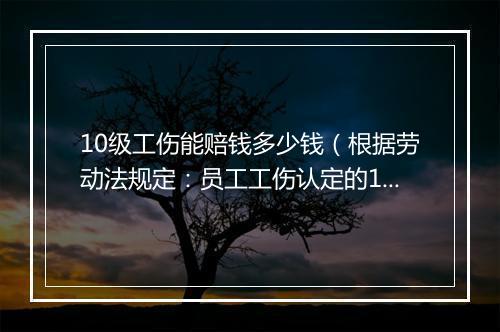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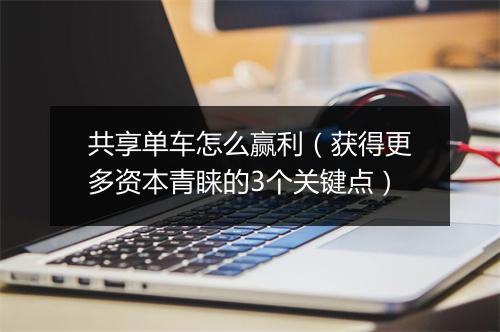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