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从各个方面解释了不同的讲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看看小编对涉疫情商事合同纠纷中不可抗力适用的审查规则的观点吧。
对疫情及相应防疫措施对合同履行的影响是否构成不可抗力的司法审查一般遵循如下若干规则:
第一,迟延履行行为在先,疫情发生在后,不可适用不可抗力免除违约责任。
研判案例发现,相当数量的案件中,当事人虽主张疫情或相应防控措施对其履行行为造成了障碍,或导致不履行状态持续,但其履行期限届满之时疫情尚未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并非造成合同不履行的原因,与合同的履行不能缺乏法律上因果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九十条第二款对此已作明确规定“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免除其违约责任。”
第二,疫情发生之后缔结的合同,应重点审查疫情、防疫措施是否为合同主体“不能预见”。
实践中,相当数量的合同,特别是标的物为涉疫物资或相关生产原料、设备的合同缔结在疫情发生之后,纠纷诉至法院后,当事人依然坚持疫情、防疫措施对合同履行的障碍构成不可抗力主张减免违约责任。无法被合同主体预见是不可抗力的必要构成要件,在疫情客观发生后,疫情及防疫措施对商事活动产生的影响已经展现,而借助发达的媒体渠道,商事主体也很容易获悉新冠肺炎及防疫措施的影响。
法律要求合同主体履行合同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亦将每一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商事主体作为理性人看待,合同主体应在合同订立和履行的过程中就已然发生的疫情和防疫措施产生的影响做相当程度的考量,案例统计反映出,因难以有证据显示合同履行受阻是因为受到了远超当事人预见能力的突发疫情或防疫措施的影响,司法审判对疫情发生后订立的合同中,疫情及防疫措施是否还能构成不可抗力持非常审慎的态度。
第三,不可抗力是“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司法实践侧重于通过审查是否存在替代履行的方式来判断疫情、防疫措施对合同履行是否构成不可抗力。
前文已经分析,疫情及其防疫措施对合同履行的阻碍主要表现出三种形式,一是主体受阻,即对具体实施合同的人的阻碍,如公司具体负责合同所涉项目的员工遭遇隔离措施;二是客体受阻,即对合同标的物的阻碍,如作为合同标的物的涉疫物资、生产标的物的工厂被政府征用等;三是合同给付方法受阻,如遭遇交通管制导致标的物无法运输交付。当主体、客体和给付方法均存在替代方案时,如可更换其他合同实施主体,合同标的物非特定种类物或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得,存在多种给付方法时,则不可抗力对合同履行的障碍并非“不可克服”。
同时商事主体在合同履行中因疫情、防疫措施而遭受上述阻碍时,应遵循诚信履约的原则积极寻求替代履行方式,不宜被动承受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免因存在替代履行可能而不能适用不可抗力规则免责,遭遇司法否定性评价。以一起标的物为丁腈手套的**合同纠纷为例,卖方主张其系受手套生产地泰国的疫情影响不能交货,属于不可抗力,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但是经审查,双方合同中并未指定标的物为泰国生产的手套,卖方应诚信履约积极组织货源完成交付,没有证据显示疫情对其履约构成了不可克服的障碍,法院对卖方主张适用不可抗力规则免责的抗辩未予支持。
第四,单纯金钱给付义务原则上不适用不可抗力规则但也存例外。
统计案例发现,存在借款合同纠纷中的债务人及**合同纠纷中的货款给付义务人以遭受疫情影响不能履行支付义务属于不可抗力为由,主张免除违约责任的情形,但均未获得法院支持。以履行内容作为区分,合同义务可以分为金钱之债和非金钱之债,大陆法系通说认为,金钱之债的不履行不能以不可抗力进行免责抗辩。这一通说的理论基础在于金钱债务的给付标的是非特定的种类物,而债务人应以其全部责任财产对该给付义务进行担保。
但随着商事交易越发复杂且环环相扣,对于金融、借贷等法律关系之外的货物**、定作承揽之类的合同,货款或其他合同价款的支付义务虽形式上也体现为金钱给付义务,但其支付义务可能有赖于其他商事交易行为。此类金钱给付义务能否适用不可抗力规则应着重考察诉争合同订立背景、债务人支付合同价款所赖的款项来源、同处于疫情影响下的合同相对方是否已经完成对待给付,若债务人确实受疫情影响直接削弱了其履行能力,可以考虑适用不可抗力规则。当金钱给付义务因疫情或防疫措施影响到了给付方法而产生迟延给付时,如需至银行柜台办理的汇款、转账、票据的交付等,应可例外适用不可抗力规则减免迟延给付的违约责任。
来源:上海二中院
对于涉疫情商事合同纠纷中不可抗力适用的审查规则的看法,文章内容就讲解到这里了,如果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那就请寻找专业律师为您解答吧!

 生活常识网
生活常识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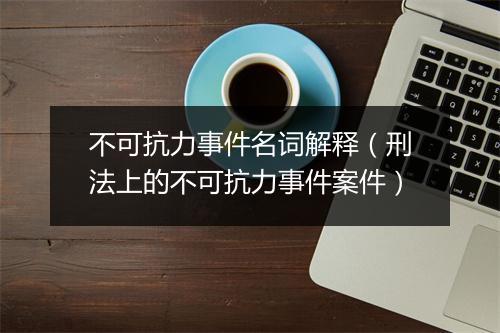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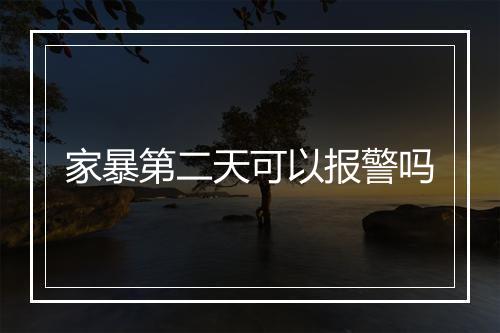














最新评论